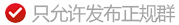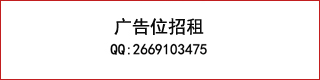9月11日下午6点,我在送外卖的时候,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。
电话里是一个女声。
她说她是我的一个读者,找我有事,问我有没有时间。
我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和微信,自己正常的生活也因此经常被打扰。
我说你先介绍下你自己,找我有什么事?
她说她关注我很久了,一直想找我,苦于没有联系方式。最近通过一个认识我的朋友,找到了我的电话。
于是就冒昧打过来了。这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,见面再说吧。
其实,联系我很容易,不必要通过电话和微信,公众号后台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会选择性地予以回复。
当然,如果手机玩得不那么顺溜,也可能不知道怎么后台留言。
我想,她也许就是属于这种的。
我说我送完手上的订单,回去还要做饭,8点以后你过来吧。
2
晚上8点10分左右,她来到我住的小区,带着一个男孩,手上提着一箱牛奶。
我在跑腿工作室接待了她。
这个女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,就把我给惊住了。
她说:我是林拔萃的孙女。
3
林拔萃是洞口的历史名人,本土老一辈的人几乎无人不晓。
在我小时候,我外公外婆,我奶奶和我姑奶奶,以及其他一些年纪大的亲友或长辈,经常说起过林拔萃。
图片
林拔萃
这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据《邵阳文史》资料记载,林拔萃生于1887年,今洞口县竹市镇车田村人,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(黄埔军校),历任国民党军队上校团长、少将师长、中将参谋长、国军高参和武冈县长等职。参与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,为培养抗日干部,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做出过积极贡献。
1949年潜去台湾,1966年在台北去世,1986年其女儿林超云(美籍华人)遵其遗愿,将林拔萃的骨灰运回家乡,埋葬在现在竹市镇车田村南边的山坡上。
图片
黄埔军校特别班第三期学生合影,摄于1937年1月28日。画红圈的为林拔萃。
4
这样一个名门之后,找我有什么事呢?
来不及坐下,她就笑着介绍自己:我叫林小菊,这是我儿子。边说边拿出一叠资料过来给我看。
资料有好几本,有《关于请求政府XXXX的报告》,有竹市镇风光图,有林拔萃其人其事简介,还有林拔萃生前居住过的房屋资料图片。
粗略看了一下,被一张图片吸引住了。
这张图片是一座高大的石刻大门,耸立在荒野之中,孤单而凄凉,像极了书本上看过的那种古遗址的存留物。
林小菊指着图片说,这里以前是我们家的老宅,叫做明德堂,建于1928年,当初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。雪峰山会战时作为野战医院,很多抗日官兵在这里治病疗伤。
解放前后,除了自己家人居住,其他都作为学校使用。后来租给了竹市粮站,直到1992年才被相关部门卖给了当地的一些村民,一夜之间拆得七零八落,之后,就成了现在这个荒凉的样子。
图片
石门上面的对联和牌匾都刻有于右任的题字。林小菊继续说。于右任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先驱,国民党元老,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,也是复旦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始人,他还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。
这些百度上都可以查到。所以说,这石门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,如果任其日晒雨淋,很快就会风化了。
我问: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呢?
林小菊说:看你哪天有时间,一起去我家老宅的现场看看。
我说好。
5
为了了解更多准确的资料,第二天,我去了县文旅广体局。
找到了文物服务中心的刘彪主任。
刘主任是个很有情怀的文物工作者,他跟我谈起了洞口诸多的文物古迹和保护情况,还有在文物维修和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。
关于“明德堂”遗留下来的石刻大门和牌匾,“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到现场去了解和堪察过,已经作为洞口的文物点记录在册,我们也在旁边竖立了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,同时,向竹市镇人民政府和车田村书记都明示了管理和安全保护责任。
这个石刻大门算是什么级别的文物?
刘主任说:准确地说,目前还没有认定为文物,只能算是一个文物点。当然,文物点同样需要保护,但具体来说,如果盖一座房子或建筑物来保护也不太现实;再说,其现在所在的土地权属也不再是林家的了。
我们建议由镇政府跟林家后人和村里协商,可以将这一片打造成文化旅游基地,这样既保护了文物,又能促进乡村振兴发展。
刘主任最后如是说。
6
第三天下午,跟着林小菊夫妇一起去了竹市镇车田村。
过了竹市那座老桥,没多久左拐,车子驶进了一片宽阔秀美的田园风光。
左边是平溪江,右边数百米开外是连绵的山丘,长满了树林。
林小菊指着山丘上的一棵古树说:听村里的老人讲,那儿曾经埋葬过几百个抗日官兵的尸骨,遗憾的是连墓碑都没有一块。有一个贵州的抗日战士,在野战医院治好了伤,娶了我们当地的女人成家立业,他女儿现在在怀化工作,经常会回来这儿,她父亲以前常常跟她说起这些往事。
大概开了七、八里路,车子停在了一座楼房前面的空坪上。
下车,沿着田间的小路往前走。
由于久旱未雨,地里的瓜果蔬菜都泛黄了,恹恹地毫无生机。
路边的野草丛里,不时能见到一块块厚重的青石,静静地躺在岁月里,永久地沉默着。
走了不到两分钟,我们就站在了图片中的石刻大门前。
图片
图片
图片
图片
数十年前,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,每天书声朗朗,人声鼎沸,欢歌笑语,炊烟袅袅,生活着一个旺盛的家族和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。
而现在,冷清落寞的只剩下满眼的荒草和枯萎的庄稼,以及偶尔越过头顶的孤独的飞鸟。
眨眼之间,沧海桑田!
仔细辨认,依稀可以看出石刻大门上的对联:
明以淡泊
德取谦和
这简单的八个字,也许是当年宅子主人的心境写照,也许是他几十年为人处世的人生信条,又或者是以此明志?
谁知道呢?
本想走近去抚摸一下历史的痕迹,无奈野藤杂草缠绕,不能进入。
转头,看见远处的雪峰山,残阳如血。
7
随后,我又在微信上联系到了林小菊的哥哥林易凡。
据林易凡说,1938年,爷爷林拔萃在任武冈县长时,因为暗中支持和配合共产党在宝庆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,因此触怒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,后来被解除了县长职务。
之后基本是隐姓埋名,不再抛头露面。
直到1992年,听原湖南省军区高参及邵阳军分区第二副司令贺锄非说起,才知道爷爷从1939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,一直跟贺司令在一起做他的军事顾问。
鉴于当时的形势,为了保全爷爷的生命安全,1950年,贺锄非送爷爷去了越南。
在越南生活了四年,又去了美国。
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,由于年老多病思乡心切,爷爷对姑姑和姑父说,自己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但那时候,根本回不了家乡。于是,姑姑姑父于1966年把爷爷送到了台湾。
在台湾几个月后,爷爷就去世了。
1986年,姑姑姑父把爷爷的骨灰送回到了家乡。
那时候,老宅明德堂的原貌还在。姑姑站在自己从小生活的家门前,睹物思人,却物是人非,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图片
1986年拍摄的明德堂背面图
8
关于明德堂的权属问题,林易凡说,明德堂占地四千平米,从建立之初到1954年,有一部分作为当地村民子弟上学之用。
解放后一直由政府代管,但并没有被没收,从1965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一直被竹市粮站借用。之后由于疏于管理,一些梁柱被偷盗导致部分坍塌,到最后被村民瓜分一空。
早在1983年,国务院有一个《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处理意见的通知》,传言要将房产还给我们,不过,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文件。
如今,一切已是过往烟云。
作为林家后人,我们希望政府能重建明德堂,利用平溪江国家级湿地公园的有利位置和品牌,将之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休闲观光的田园式美丽乡村,既可传承历史,弘扬文化,又能给家乡人们带来经济效益,为乡村振兴打造样板工程,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措!